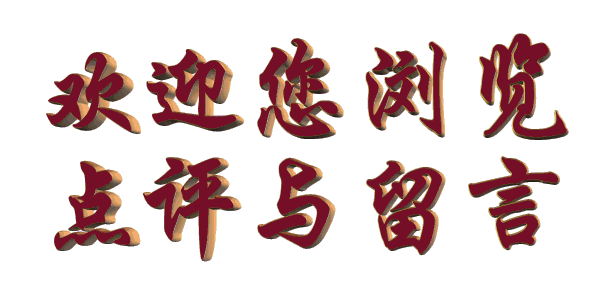不管你是宅男、屌丝男、还是貌若潘安的美男子
不管你是御姐、腐女、萝莉女、还是傲娇的女王
自己只能刷微信微博看靓照?对这些统统说no!
只要你有勇气晒出自己的照片并邀请好友来投票,就有机会赢得现金大奖!
我有我风采,为什么不秀出来!
晒出手机自拍照,
用自己的气场HOLD住微信圈,
让个人的魅力无限扩散!

中篇小说
三去珍珠岗
作者: 张天真
珍珠岗是一个四等小站,和它的名字一样,像一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长白山南麓的一个山梁上。山下,是日以继夜奔泻流淌的滔滔的松花江,山里人管这条江叫老松江。这是一条从长白山天池飞流而下的江,它水流湍急,一路宛延曲折,流经吉黑两省,进俄罗斯入海。珍珠岗只是长白山里的一个小站,全站只有三条铁路线,其中一条铁路是通往铅锌矿的专用线。铅锌矿离火车站足有10多里地,那里有农贸市场,有饭店,商店……是全珍珠岗最繁华的商业区。
我总共去过三次珍珠岗,头一次是在一个充满生机,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春季去的,是受路局领导的指派,到珍珠岗采访珍珠岗车站万天无事故的经验。
火车穿山走林,在崇山峻岭中盘旋而上。从江城一开车,火车就开始步步上坡,到珍珠岗的时候都几乎到了山顶了。这一路真是满目青山满目绿,到处都是看不够的迷人景色,听不够的啁啾鸟鸣。那一山山翠绿再配上石砬子上的一簇簇粉红色的映山红,红花配绿叶,彰显山川的美妙,大地的风彩。满山翠绿一点红,珍珠岗被大自然的能工巧匠点缀得更加绚丽多彩,婀娜多姿,像画卷般的美丽景色。因快车到珍珠岗不停,我坐的是一趟慢车,站站停。虽然时间紧张,车速很慢,但我还是没坐够。因为这一路的山川秀丽,景色迷人,空气清馨宜人。火车到达了珍珠岗车站,这个车站下的人很少,大部份都是铅锌矿的员工或家属。一下车,首先浸入肺脾的就是一股清新芳香的味道,和听到的“哗哗”流淌的水声。这大山里的空气就是好,在这里有我们城里,尤其是重工业城市少见的蓝蓝的天,绿绿的树。松花江是由从天池流淌下来的神水飞流直下,形成清澈见底的潺潺溪流而逐渐拓宽,然后,又形成了一条浩浩淼淼的大江。珍珠岗下就是那哗哗流淌了几千年的老松江。过了珍珠岗,就再也见不到高山了,那连绵起伏的是丘陵,那绿茫茫,一眼望不到边的是茫茫林海,这里已经是海拔二千多公尺的山巅了。站前共计有十一家住户,一遛小平房是这个车站的家属宿舍。珍珠岗是个四等小站,车站共有十二个职工,其中站长家住在离这二百多里远的松江镇。他每天跑通勤,往返于松江——珍珠岗,也颇辛苦。小站没有吵杂的声音,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是每天一趟火车一到,算是给这个小站带来了热闹,带来了生机。火车还没有进站,这里的娘们和孩子就早早的在车站等候了。人们一下车,大人孩子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的感到每一个旅客都是那么的新奇。一点不经意的事也会引起这些人的笑声,孩子们更是好奇,他们会跟在生人的后面一直跟到老远老远,像是观看希奇古怪的动物一样。我下火车以后就直奔站长室走去,没有孩子跟我。本来我来之前应该到大龙山车务段打个招呼(珍珠岗归大龙山车务段管),可我没有,因我经常下来采访,对沟里的小站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对这里的每一个人我都如数家珍般的了解他们.我听车务段劳资主任向我介绍过这里的每一个人。虽然珍珠岗我是头一次来,但是沟里小站的人和城里人大相径庭,他们都是那么热情待客的。我这次来采访的对象是一个在珍珠岗建立那天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勤勤恳恳,万天无事故的一个老工人,扳道员毛永忠老师傅。
老毛头今年已61岁了,还有几个月就到了退休的年龄,是铁路局树的安全标兵。在局职代会上我见过他的面,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是一个高挑个,背有点驼,刀条的脸,一笑满脸的沟沟岔岔里有洋溢出一种满足的感觉,一身洗得发了白的工作服像是租来的一样,五冬六夏的穿在身上。上次和他见面距今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今天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顶班?
火车开走了,小站又恢复了以往的沉静,我背着兜子往站长室走去。
站长室门口站立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向冷冷清清的站台上四处撒目。我离站长室还有十几米的时候,小伙子就发现了我这个不速之客了。他笑眯眯地迎了过来,问:“您是路局来的领导吧?我们段长来电话了,说是您这几天要来!”小伙子热情地和我握手,并向我介绍说:“我姓娄,叫娄高松,你就叫我小娄的吧,我在这个小站管点事,小名叫站长。冒昧地问一下,领导贵姓?”小娄很有礼貌,人很谦虚。
“我姓朱,叫朱宏,你叫我老朱吧!”我也自我介绍说。
“那不好,听说领导是局报社的,请问官称怎么称呼?”
“什么官称,我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记者,你就叫我老朱就行了,叫官称倒觉得不自在。”我从来就不喜欢别人叫我官称,受拘束,受限制。没有人称呼我的官称我会觉得很放松,无拘无束。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没事先通知大龙山车务段,更没去大龙山车务段,就直接在珍珠岗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通知了大龙山车务段长,搞得我还很被动。
我和娄高松在外面寒喧了几句后就进了站长室,几个调皮的孩子也随后跟了进来。站长室很简陋,一张桌子,上面放了几部电话,地上有一把转椅,边上放着一个长条凳子,站长室的里面有个小套间,那里放了一张床,显然是娄高松住在站长室了。几个小男孩进了站长室,毫不客气地,齐刷刷在长条凳子上坐下。几双天真幼稚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仿佛是在看一个外星人。娄高松笑一笑,说:“领导同志,按年龄我应该管您叫大叔,既然您不愿意透露您的官称,那我就不客气了,管您叫朱大叔吧!”
“好哇,这个称呼好,即亲切又随便,我十分欣慰地接受。”我喜欢别人这么称呼我,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感到亲近,才能放松,才能无话不谈。娄高松给我沏了一杯茶水,一劲儿让我坐在他的转椅上。我和他互相谦让了一会儿,娄站长说:“朱大叔,真不好意思,小站条件差,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没关系,挺好的。”我和娄高松互相谦让了一会儿,倒谁也没坐,娄高松瞅瞅那坐满了一凳子的孩子,笑着说:“走吧,都回家去吧,这有什么好看的,一点儿礼貌也没有,来客人了你们倒把坐给占了。”娄高松的话刚说完,那个大一点的孩子站了起来,指指他刚刚倒出来的位置,说:“请叔叔坐。”另外几个孩子就象是没听见似的,还在盯盯的打量着我,娄高松无可奈何,尴尬地笑一笑说:“这个地方的孩子很少见到生人……但他们却都自来熟。”
“所以,一见到生人就像见到了怪物一样?”我打趣说。
“可不是咋地,巴掌大个地方,没见过世面。”娄高松也笑了。不知不觉,时间已接近中午了。我瞅瞅表问:“娄站长,那个毛永忠师傅今天是什么班?”
毛师傅是我师傅,今天是休班。本来师傅都马上要退休了,段里照顾他,让他提前回家休息,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说啥也不干,非要站好最后的几班岗。今天他休息,这不,去矿上给食堂买菜去了!他呀,只要一有空,就总在车站呆的。朱大叔,刚才下车时您没看见俺们车站那个花园吗?那就是毛师傅莳弄的,他呀,可真是以站为家了。”娄高松提到花园我才想起来,一下车我就看见了那个规规整整,有凉亭花榭,石头铺地的小花园了。别看这个花园小,可它却代表了这个小站的精神面貌。正在我和娄高松说话的时候,门外背包罗散的进来一个人。一进门这人就嚷嚷开了:“咳,今儿个可赶巧了,一进市场正赶上一份新杀的猪,今天中午咱们改善改善伙食,有新鲜的猪肉,刚出锅的大豆腐。”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永忠。他也认出了我:“小子,这不是老朱兄弟吗,刚到呀?”
“刚下车,这不,我和娄站长正在念叨你呢。这人不抗念叨,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我上前要和毛永忠握手,可他却把手缩了回去,说:“不用客套了,我的手埋汰,上矿里转了一圈,又买菜又帮人家干点活,这不,害怕耽误午饭,我连手都没洗就回来了。正好,来得好不如来得巧,算你有口福,赶上俺们中午改善伙食,就在俺们食堂吃吧!”
“好哇!那太好了,正好,我尝尝你们厨师的手艺!”我很喜欢在车站的小食堂吃饭,现在,路局各个车站都有自己的小食堂,方便了职工。
“什么厨师,是我自己做的,好赖大伙不嫌弃,将就吃呗!”毛永忠憨憨地笑了。这时,娄高松又说:“俺这个食堂原准备雇个做饭的,这不,师傅说啥不让,这做饭买菜的活让他和师娘给包下了。平时呢,都是师傅做,赶上师傅顶班就师娘来做,给师娘开工资又说啥也不要。”
“给什么钱,咱们一个四等小站钱也不宽裕,只要把生的做成了熟的,大家不用带饭就行了。我不图稀别的,给大家减少点负担。”毛永忠放下菜,换了衣服就要下厨房。娄高松又在夸毛永忠:“我们这个小站最忙最累的顶数师傅,他为了给车站省钱,连师娘也给拽来了。我们这个食堂开办了整整四年了,师傅就和师娘整整在食堂默默地奉献了四年……”
提起毛永忠,娄高松总是赞不绝口,总有说不完的话,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
“好啦,小娄的,别给我评功摆好了,我得赶紧去做饭,待会儿老朱在咱这吃吧?”毛永忠拎起菜要往厨房去。
“师傅,你做你们吃的就行,我和老朱大叔去矿上吃去。”娄高松说完站起来就要和我走。
“别介,矿上太远,咱就在你们的小食堂吃,我看挺好,我也好品尝品尝毛师傅的手艺。”
“别,咱还是上矿里吃去,管咋地那里有正经饭店,正经的厨师,走吧!”娄高松说走立刻就要走,我可不想去,十里多地去吃顿饭,得不偿失。正像人们所说,吃肥了,走瘦了。再说了,我的任务是来总结经验,决不是为了吃喝而来。
“我看老朱说的就对,咱们的小食堂虽然简陋了点,但它卫生,干净呀!”毛永忠也让我在他们的小食堂吃饭。娄高松见拗不过我们俩,也只好作罢,来了个主随客便。
我们来到了车站小食堂。嗬!小食堂不大,连厨房和餐厅加一块不到十平米。但却收拾得窗明桌净,墙上贴着白瓷砖,地上铺着大白地砖,没有一点灰尘。毛永忠一进厨房就开始忙火起来,我也不能干闲的,帮的打打下手,摘菜洗菜。毛永忠说啥也不让我动手,我哪能让他一人忙活呀,不由分说就动起了手。不一会儿的功夫,毛永忠做了四菜一汤,还没等饭菜端上来,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充溢了餐厅。
“吃饭,来。”毛永忠把菜端上来说。“老朱,将就吃吧,我们小食堂没有酒,我回家给你取一瓶去。”
“别,毛师傅,我不喝酒,你也别取了,来吧,咱一块吃点饭吧!”我给毛永忠拽个凳子。毛永忠洗洗手就要走:“不啦,老伴在家做好了,我得回去吃饭了。”
娄高松站起来拽住毛永忠的手,说:“师傅,平时你不在这吃也就算了,今儿个是来了贵客,您就在这吃吧,陪朱大叔吃顿饭,你们老哥俩儿好好叙叙旧。”
“有你在这陪不就行了吗,我就不用了,叙旧有的是时间。”毛永忠执意要回家。我觉得很不过意,就站起来,说:“毛师傅,坐下咱们一块儿吃吧,也好唠唠嗑。”
不论谁也挽留不住毛永忠,他还是回家了。临走时,把那几个调皮好奇的孩子叫上,说:“走吧,都回家吃饭去吧。”那几个孩子这才恋恋不舍地跟着毛永忠回家吃饭去了。娄高松无可奈何地晃晃脑袋,说:“我师傅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只有中午顶班的时候才能在这吃一顿饭,平时他从来不在这儿吃,连我师娘也一样,从不在这儿吃。他曾经说过,他如果在这吃饭,有贪小便宜之嫌疑。”我听了娄高松的话,顿时觉得肃然起敬,不无感慨地说:“这就是老一辈人,他们无论当官的,还是当工人的,都特别清廉,奉公守法,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向来都是分明的。”说到这,我倒觉得似乎说走了嘴,是不是守着痤子说矮话呢?人家娄高松好赖不济也是个站长呀,别让他有别的想法。我知道,娄高松是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到小站只不过是过渡,暂时来镀镀金,过后指不定能够发展到什么地位呢。我的话也是敲敲警钟,也叫警钟长鸣吧!告诉他以后官做大了要做清官,不要做贪官。娄高松听了我的话频频点头,又莞尔一笑,认真地说:“朱大叔说的对,老一辈人就是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学习的,自从我来到珍珠岗,和师傅学到了怎么做人,怎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他的敬业精神。”
“我只不过是信口开河的那么一说,别介意呀!”我说。这时候,午餐时间到了,当班的工人陆陆续续的回来吃饭了。统共每天中午吃饭的人才五个,可能是因为我来的缘故吧,大家都很受拘束,没有人说笑打闹。除了我和娄高松在唠嗑外,这顿饭吃得很严肃。我知道,虽然工人对我很尊敬,但那只是敬而远之,大家对上级领导的到来有点麻木不仁,甚至是讨厌,反感。
吃完了饭,娄高松执意要我到站长室去喝茶。盛情难却,我也只能悉听尊便了。我和娄高松回到站长室,他给我沏了一壶铁观音。我瞅瞅站长室的里屋放着一张床,就问:“小娄的,你晚上也不回家?”
娄高松笑一笑,说:“不回去,我吃住都在车站,我家住在大龙山,如果要跑通勤的话,那整个时间就都浪费在道上了。也没有媳妇孩子,我干脆弄张床,吃住就都在班上了。我们这的条件差,没有啥好吃的,买点菜都得到矿上去,今天你赶巧了,往常我们这就是大豆腐,豆腐泡、干豆腐,大家都吃腻了,都管师傅叫老毛豆。过两天就好了,山菜一下来,师娘成天上山采山菜,我们一顿能吃好几个菜呢,今天朱大叔也没吃好。”娄高松表示歉意。我们俩正在喝着茶水,唠着嗑的时候,只听外面吵吵巴火的来了许多人,这些人说话的功夫就进了站长室。嗬!原来是毛永忠夫妇来了。毛永忠老伴是来刷碗洗马勺准备晚饭的,身后又跟了四个小孩子。毛永忠进屋就问:“老朱,吃得咋样?”
“不错,毛师傅的厨艺决不亚于饭店厨师的水平。”我说的是心里话,毛永忠的厨艺真的不错。
“真的吗?”毛永忠很高兴。
“真的,决不是奉承。”我敢肯定,我说的是心里话。
“那好,那你在这呆的这几天就在这吃吧,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炒菜。”
“师傅,这几天就辛苦您天天往矿上跑啦!”娄高松的意思是让毛永忠到矿上的集市买点好吃的。我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急忙说:“别介,别为了我跑那么远的路,我这个人嘴壮,有啥吃啥,只要能填饱肚子,我吃啥都无所谓。”
“别,俺们也都跟的借点光,改善改善伙食。”娄高松说。
“是呀,大伙也都跟的改善一下伙食。”毛永忠随帮唱影。
“吃的问题解决了,这几天老朱大叔就在我的床上委屈几天吧!”
娄高松把他的床让给了我。说实在的,在这个只有11户人家的小站,附近连个旅馆一类的住宿的地方都没有,我真没有地方住。但我又不忍心让娄高松来回跑通勤,就推辞说:“别,你还是在你的床上睡,我去矿上,那里不能没有旅店吧?”
“有是有,就是太远了,你走不起。”娄高松还是坚持让我睡他的床。就在我们俩人互相推让的时候,毛永忠老伴说了话:“好啦,你们俩儿谁也别谦让了,我看这样最好,如果老朱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到我家去住吧。”毛大嫂的话刚说到这,跟她们一起来的四个小孩一齐上来拽我,这个说:“上我家去住吧,”那个也说:“俺家有地方,上俺家去住吧!”山里人的热情好客,着实让我感动。还没等我作决定,毛大嫂就把事定下来,说:“就这么定了,老朱这几天在我家吃,我家住,你也别推辞了,我决定了!”毛永忠瞅瞅老伴打趣的说:“还是老伴想得周到,我咋就没想到呢?走吧,俺家一号首长发命令了,你也无条件执行吧!”
毛大嫂不容分说就自作主张的把事定了下来,娄站长也十分赞同。既然已经尘埃落定了,我还有啥话说呢?只能客随主便了。正好,这也是一个采访的最好的机会。我这次采访的时间是一个星期。我在毛永忠家住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可把毛永忠累够呛,一有空就往矿里跑,去采购一些他们平时舍不得吃的好嚼咕。我真的感到很过意不去,就一劲向毛永忠说些客套的话。谁知,毛永忠却感到很不满意,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老朱,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不要太客气太谦虚了行不,人们常说谦虚大了就是虚伪,我看你就是虚伪,虚伪的都不冒汗。”时间长了,毛永忠和我厮混熟了,不习外了,和我开起了玩笑,这倒使我感到很亲切,就随便回敬一句:“毛师傅,你看我不冒汗了吗,我冒的不是虚伪的汗,而是感动的汗,被你们的真情感动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结束了这次采访,这一个星期,我和毛永忠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他顶班了,我就跟他去报道房。他做饭,我跟他去厨房,同桌吃饭,同炕而眠,感情愈来愈深。要往回走的时候,真的有些恋恋不舍了。走的头一天晚上,正赶上毛永忠休息,他特意准备了一桌好菜,把娄高松也请了过来,说啥要为我践行。
酒桌上,毛永忠和娄高松都盛情地挽留我多住几天。毛永忠老伴在厨房忙做完了菜,我和娄高松都让她上炕一起喝
酒,她笑一笑,说:“不行,俺们山里的规矩,女人是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的,更不能一起喝酒了,那要是让人看见成啥事了,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呀!”听了毛永忠老伴的话,我和娄高远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说:“老嫂的,那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现在都啥年月了,可不兴那一套了,快上来吧,没人笑话你的!”
“是呀,师娘,您老总在大山里呆的,外面的世界都发展成什么样了您都不知道?在城里,别说男女在一起喝酒了,女人也不耽误喝醉酒,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到。”娄高松也一劲让毛永忠老伴上炕一起喝酒,我们两个人再三相让,毛永忠老伴还是不肯上桌一起喝酒。我一劲向毛永忠使眼色,意思是让他开口,他的话老大嫂准听。毛永忠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笑一笑,表情很诡密地冲老伴说:“行啦,别装大尾巴狼了,人家一个路局的领导,一个站长都这么让你上桌,你还拿什么褶呀,上桌吧,从今儿个干始,咱们就破一破那个老规矩!”
“是呀,那都是过去那男尊女卑的陈规陋习,早就应该破了,来吧,大嫂上炕吧。”我一看毛永忠发了话,赶紧给大嫂让了个座。毛永忠老伴这才慢腾腾,唯唯喏喏的上了桌,挨的毛永忠坐下了,娄高远赶紧给她的杯里倒满了酒。
我们喝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和娄高松都被毛大嫂灌得酩酊大醉,确切地说,我们是在平等喝酒的情况下,我和娄高松败下阵来,成了毛永忠老伴的手下败将,毛永忠笑了。第二天早晨,我要往回走了,临走时,毛永忠和我愧疚,欠意地说:“我说老朱呀,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呀!”
“没啥,又不是嫂子灌的,是我的酒量不如嫂子。嫂子的酒量可是十分了得呀,我是甘拜下风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毛永忠得意地笑了,说:“她呀,是轻意不出手,一旦出手就没有对手。”说到这,他又更正一句说:“我是指在我们这个小站一亩三分地,在别的地方咱可不敢说,那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呀,按文词叫什么来着?”
“山外青山楼外楼。”娄高松接过话茬。
“对,就是这个意思!”毛永忠笑着说。
这次来珍珠岗收获颇丰,即收集到了不少的经验材料,又采集到了不少的感人的事件,对我今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
我还没等走,外面就吵吵嚷嚷的来了许多人。
“外面干嘛这么吵?”我疑惑地问。
“听说你要走了,这不,左邻右舍的都送你来了,在咱们这个小站你可是他们见到的最大的官了!”毛永忠的话里显出了那么一丝的得意来。
“别瞎扯了,我算个啥呀,是你们把我看大了,其实我就是仓海一粟,是苍蝇蚊子一样大的官,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我绝对不会像苍蝇蚊子那样遭人痛恨,让人恶心。”我对于毛永忠的夸奖觉得自惭形秽,赶紧尽量贬低自己。
“怎么样,又谦虚大了不是,又虚伪了不是?你是上头派下来的人,你要是苍蝇蚊子,那俺们这些草民可就连苍蝇蚊子都不如了!”
“说哪里的话呀,你们是最基层的群众,是基础,基础好不好是决定高楼大厦质量的最根本的保证的。只有夯实的基础才有高楼大厦的千秋永固!”我的话听起来有点官味十足,夸夸其谈,很别扭。毛永忠只是频频点头,再没有插话,只听我一言堂了。说话的功夫,几个小孩子很快先进了屋,另外几个家属也随后进了屋。孩子们围着我,他们都仰起小脸在望着我,那充满稚气的眼睛是流露出对我的恋恋不舍。这些家属都是小站职工的妻儿,他们有的拿着晒干了的山菜,有的拿着刚刚挖的婆婆丁。
火车快进站了,大家送我去车站,孩子们抢的给我拎包。从毛永忠家到火车站没有二百米,三五分钟就到车站。大家簇拥着我来到了车站。娄高松早已在车站等的送我了,没唠上两句嗑,火车便进站了。我上了火车,毛永忠拉着我的手,问:“还啥时来?”
“说不准,可能三年五载,也可能三两个月。”
这个四等小站火车只停一分钟,即停即开。咦,奇了怪了,我咋没看见毛永忠老伴呢?我正在纳闷,只见毛大嫂老远的,急匆匆的跑来。她的手里拎了一包东西,等她气喘嘘嘘的跑到跟前时,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说:“老朱大兄弟,这是我刚刚给你攥的酸汤子,我用凉水拔了一下捞出来的,你拿回去用开水烫一下就能吃了,拿回去给弟妹尝尝!”
“不用了,这几天太麻烦你们了,我真的有点过意不去了。”我对山里人的质朴,盛情,感到不过意。一股股暖流涌透了我的全身,这就是山里人,他们有着纯朴,热情,奔放的性格,他们的好客让你感到了宾至如归,温暖如春。火车开了,我拿着毛大嫂送给我的酸汤子条,望着站在站台上向我摆手,热情洋溢的人们,想起这几天朝夕相处,心里觉得有点酸酸的。开车前紧紧握着我的手的毛永忠问我还啥时来的话让我的心里格外沉重,我想,等我再来的时候毛永忠老师傅恐怕就已经退休了,下次来的时候小站不知是个啥模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四等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人们的热情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人们常说,时间是离弦的箭,是什么箭,是火箭,而不是弓箭。无论什么箭,都足以说明,时间的速度把人们很快变老,一代又一代。
五年之后的一个冬天里,我第二次来了珍珠岗。上次走的时候,毛永忠给我留的电话号,临走前我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里告诉我,查无此号。我想,可能是毛永忠退休以后搬出了大山。珍珠岗山高林密,手机用不了,没有信号。我一下火车就直奔站长室,这次来是到大龙山采风,本也不想到珍珠岗,是顺路,我是想看看老朋友。等我到站长室的时候得知,娄高松就在我走的第二年就调到大龙山车务段当上了段长。(是大段长)我又打听毛永忠,新来的站长也是毛永忠的徒弟,姓胡,叫胡伟军,来这个车站当站长也有四个年头了,是个近五十岁的老调车长提升的,说是就地取材,旱地拔葱,在珍珠岗提起来的,是毛永忠的大徒弟。我上次来就认识了他,也采访过他。他告诉我,师傅早就退休了,但现在人还没有走,还在义务为车站小食堂炒菜做饭。我打心眼里佩服毛永忠,人都已经退休了,还在车站发挥着余热。我急于见到毛永忠,这次来的时间匆忙,时间很紧,急于看看毛永忠和娄高松。
就在我和胡站长闲唠的时候,外面响起了自行车铃声,只听有人喊:“小胡,快来帮我卸菜。”
我听出来了,门外是毛永忠的声音,地地道道的青巴菜味:“小胡,铃都响了,咋不出来帮我拿菜呢?”
“师傅回来了,咱不告诉他,给他个惊喜。”小胡悄悄和我说。我们俩儿谁也不吱声。
“嗬,你小子和我俩儿藏猫猫咋地。”毛永忠边说话边往下拿菜。等他把菜都卸下来后,径直拿到了食堂。他把菜运到食堂后才来站长室,边走边说:“好小子,官升脾气长啊,不出来帮我卸菜。”小胡赶紧示意我猫起来。我急忙躲进了里屋。毛永忠一进站长室就亮开了他的大嗓门,大声嚎气地嚷嚷说:“小胡,你小子咋啦?”
小胡强忍住笑,冷丁从里屋窜出去,说:“师傅,你看谁来了?”
我坐在里屋床上一动也不动,故意把身子转了过去,免得被他认出来。
“谁来了,是稀客呀?”毛永忠直接进了里屋,他瞅着我的背影,问小胡说:“我说小胡,这人的背影有点面熟,是哪位贵客呀,稀的上俺这深山老林里来?”
我还是不吱声。小胡“嘿嘿”笑着说:“师傅,您猜猜!”
毛永忠对着我的背影仔细的打量了一番。我屏住呼吸,忍住笑,尽量不吱声。毛永忠摇摇头,说:“猜不出来,行啦,你俩儿别卖关子了,这位兄弟快把身子转过来吧!别把俺急坏了!”
我再也忍俊不住了,就把身子转了过来。看见是我,毛永忠咧开大嘴“嗬嗬”的笑了起来,嘴里一劲说:“哟,是老朱来了,咋不事先来个电话呢?”
“咋没给你打电话,你家的电话无法接通。”我埋怨说。
“哟,你瞧我这记性,怨我啦,我家的电话号换了,忘了通知你了,等今天晚上喝酒我自罚一杯!”毛永忠一劲儿表示歉意。
“师傅,您陪的老朱大哥唠会儿嗑,我给你们沏壶茶水,正好这节骨眼也没有车了,咱好好唠唠。”一见毛永忠和我唠上了,小胡急忙烧水去了。就在我和毛永忠去屋里唠嗑的功夫,外面的天阴了,满天的阴霾,屋里越来越黑。毛永忠把灯打着,不一会儿的功夫,天上飘飘洒洒的下起了大雪,雪越下越大。小胡把茶水沏好,拿起条掃,说:“师傅,您陪的老朱大哥唠嗑!”
“你这论的是什么辈?我和老朱是哥们,你也管他叫大哥,没大没小!”毛永忠不满地白楞徒弟一眼。
“别介,不怪小胡,咱个论个地,本来我也比小胡大不了几岁!”我赶忙纠正毛永忠的话,给小胡个台阶。听了我的话,小胡小声嘟哝一句:“本来吗,个论个地呗!俺俩儿也差不了多少。”
“胡站长要上哪儿?”我问。
“老朱大哥,千万别叫我胡站长,就叫我小胡就行,大家都叫我胡闹,要不然你就叫我伟军吧!”小胡是个很风趣的人,他边说边往外走,走到门口和毛永忠说:“师傅,您陪的老朱大哥喝茶唠嗑,外面的雪下的太大了,我上两头板道房扫扫道岔。”胡伟军刚刚走出去,又转回来问:“师傅,今儿晚上咋安排老朱大哥?”
“你别管了,让他上我家去!”
“那带我不?”
“又想到我家蹭饭,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毛永忠故意绷着面孔。
“我不管,今晚上有酒喝了!”胡伟军在师傅面前像个小孩子。
“美的你!快扫道岔去吧,呆会儿1504次就进站了。”毛永忠瞪了胡伟军一眼,撵他走。
胡伟军瞅我笑了,冲师傅作个鬼脸,伸伸舌头,转身走了。毛永忠瞅着徒弟那宽厚的背影,即喜爱又骄傲地说:“这小子,还像个孩子,干工作真是个好样的,从来不用操心,就是在我面前总也长不大,这不,都年近五十了,还像个孩子!”
“是呀,徒弟在师傅面前永远也长不大,就像儿子在父母面前一样,永远都是孩子!”从刚才师徒二人的对话里我看得出这师徒二人的感情笃深。
“待会儿1504次车过去就没事了,今天晚上就再也没有车了,小胡也休息了,等他回来咱一起到我家,咱哥俩好好喝两盅,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让你老嫂子陪你喝。”毛永忠故意搬出老嫂子来吓唬我,说实在的,五年前那一次我真的是头一次见过能喝那么多酒的女人,我真的是即佩服又让老嫂子给吓住了。听毛永忠说让老嫂子陪我喝酒,就急忙说:“不用,可不用嫂子聪我,那年让嫂子陪我喝酒都把我陪醉了,丑态百出,掉老价了!”
“嘿……”毛永忠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解释说:“老朱,你理解错了,这次我决不能让你喝多了。我的意思是,自打那次以后,我们家一下子就破除了过去的老观念了,客人来了你嫂子也可以上桌了。现在你嫂子的年龄也大了,酒也喝不动了,别害怕!”
“早就应该破除那些陈规陋习了。”我赞许地说。
“是呀,那都是一些王八屁股生疮——乱规(龟腚)定呀,是应该破了。”说话的功夫,外面就已经放黑了,雪还在下着,雪片像春天的杨树絮,飘飘洒洒,漫天飞舞。毛永忠不时的看看墙上挂着的石英钟。又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对我说:“老朱,你饿了吧?”
“不饿,不饿。”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的肚子已饿得“咕咕”叫了。
“再等一会儿。”说到这,毛永忠也拿起一把扫帚,对我说:“你稍坐,我出去帮他扫扫,这雪看来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我去去就回来。”毛永忠把领子搊一搊,就钻进雪夜里。我也急忙跟了出去:“毛师傅,我也去。”
“你就别去了,雪太大,线路不好走。”毛永忠说啥也不让我去。说实在的,这老大雪,我不在便罢,我在这就绝不能让毛永忠六十多岁的老人一跐一滑,深一脚浅一脚的自己走了。我执意要和毛永忠一起去扳道房,就在我们俩要往扳道房走的时候,大雪中走来了胡伟军。他的身上披着白雪,趁着夜色远远望去,像一个白白的北极熊向我们走来。快到跟前的时候胡伟军才说话:“师傅,你们上哪儿去?”
“扫道岔去。”毛永忠说。
“快领朱大哥回家去吧,就这点活都不够俺们干的,快回家吧,这么晚了,朱大哥该饿了,别忘了,呆会儿我也去呀!”胡伟军说完又往前边的扳道房走去。
“走吧,老朱,回家吧!”毛永忠顺从地听了徒弟的话,要和我回家。这时,起风了,西北风卷起地上树上的积雪向我们扑来,我顿时觉得浑身凉嗖嗖的,山林被风刮得发出怪异的响声。
“毛师傅,咱们回家好吗?”我问。毛永忠瞅瞅天,肯定地说:“走吧,起风了,云彩开始抓堆了,用不了多一会儿,天就晴了。”我听了他的话觉得很佩服,这是山里通,山里的天气千变万化,本来是扬风交雪,冷风嗖嗖的天气,瞬息间就可以变得满天星斗,晴空万里。我信服毛永忠的判断,便跟他去了他家。
毛大嫂还没吃饭,做好了等老伴回来吃饭。我们一进屋,就觉得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这就是东北的特色,无论外面多么寒冷,哪怕是天寒地冻,零下30多度的天气,一进屋就觉得暖融融,热呼呼,让人感到了春意盎然,暖意融融,家的温暖。起初,毛永忠老伴先是一楞,但旋即就认出了我,便热情地开始嘘寒问暖。毛永忠急忙吩咐老伴:“喂,老婆的,快把鹿肉拿出来切一切,再炒几个鸡蛋,你都做了什么菜?”
“我烀的地瓜土豆,干豆角燉肉,炒的大豆腐。”毛大嫂边说边把桌子放下,对我说:“老朱大兄弟,上炕头坐,俺家的炕可暖乎了,先暖和一下,我先给你们沏点茶水,赶忙就炒菜。”
“嫂子,别忙活了,吃点现成的吧,别费事了。”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费啥事呀,也都是些现成的,鸡蛋是自己的小鸡下的,你有口头福,正好,姑爷给送来的鹿肉,尝尝鲜。”毛永忠老伴边说边进了厨房。片刻功夫,茶水沏好,菜也都端了上来,我和毛永忠边喝茶水边等胡伟军。别看毛永忠说没带胡伟军的份,可吃饭的时候他却是不见胡伟军不动筷。一杯茶还没喝了,门外有了动静,不用说,是胡伟军来了。他一进屋就用鼻子嗅嗅说:“呀,什么味这么香呀?”
“就你鼻子尖,一进屋就闻到了。”毛永忠老伴笑着指指胡伟军的鼻子说。这时,有火车铿锵通过的声音。
“道岔都扫干净了?”毛永忠问。
“放心吧师傅,你徒弟干活啥时不利索过?”胡伟军说着话,自己到碗架拿了一个二大碗,一下子把茶壶里的茶水倒了一大半。边倒水,嘴里边镇镇有词地说着风凉话:“没人给咱倒,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呀!”
“别臭美了,自己不动手还得让我这老太太侍候你呀?”
“那可就不对了,师娘不一视同仁,你咋就给老朱大哥倒茶水,为啥不给我倒!”胡伟军在师傅师娘面前俨然是个调皮的孩子,他的话说得师娘“扑哧”笑了。
“你呀你呀,让你喝就不错了,还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告诉你吧,老娘我就不给你倒,爱喝不喝,你能和老朱大兄弟比吗?人家是客人,你是自己家人,还好意思叫师娘给你倒水,我没让你倒水就不错了。”毛大嫂的嘴从不让人,她和胡伟军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逗起了笑话。
“好啦,你们娘俩儿别逗了,老的没个老的样,小的没个小的样,两个都没正形,来吧,小胡倒酒。”毛永忠对胡伟军说。我们三个人坐下喝了起来。这次毛永忠老伴可没客气,她搬了个凳子,在炕沿边坐下。
“老嫂子,上炕喝吧,炕上暖和。”我往炕里挪一挪,让毛大嫂往里坐。
“不用,我上炕谁侍候你们呀?”
“我们自己来。”我说。
“你们都行,就这老头的事儿多,一会儿水一会儿尿的,可难侍候了。”毛大嫂说话很幽默,像是说单口相声。
“好啦好啦,闭上你那碎嘴子吧,喝酒。”毛永忠开始发号施令了。
我们四个人开始喝酒了。两杯酒下肚,毛大嫂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像老松江的流水,奔流不止,一发不可收拾。她是在发牢骚,好像要把憋了许久的话一股脑的倒了出来。
她先是说娄高松忘恩负义,当官不认人。后来又说毛永忠费力不讨好。气得毛永忠一劲儿瞪她,她佯装看不见。一会儿又说,儿子叫他们到城里去住,可这老头就是舍不得离开珍珠岗。毛永忠见老伴喋喋不休的说起没完,就把话接过去说:“城里我住不惯,我离不开珍珠岗,离不开干了大半辈子的小站,离不开大山,离不开绿水。这个珍珠岗从打开线以来我就一直在这干!”
我听毛永忠老伴满腑牢骚的话里有弦外之音,有许多委屈,就问:“老嫂子,那个娄高松现在不是在车务段当段长吗?”
“是呀,人家大发了,去年高升了,现在是车务段大段长啦!”
“是,人家大学毕业能不高升吗,又有根基,无论多大的风浪也动摇不了人家呀!”从毛永忠老伴的嘴里我听得出她的画外音,看来,她是对娄高松相当不满意。
“行啦,你少说两句吧,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人家娄段长有文凭,有水平,工作肯干,他就是块当段长的料。”毛永忠对老伴很不满意。为了不让老伴继续发牢骚,毛永忠故意岔开话头,问我说:“老朱,这次来又是总结经验还是采访点什么?”
“我这次来是别的事,本来我是到长白山采风的,挺长时间没看见老朋友了,顺道来看看,以后机会也不会太多了,我再有两年也退休了。”因年龄不饶人,我感到很伤感。
“老朱,说实在的,还是咱们这茬的老人讲感情,还知道到这大山沟里看看老哥,够朋友,够哥们。”我能来珍珠岗看他,毛永忠格外高兴,酒喝的多了,舌头打卷了。他已退休,有点失落。我的心里也一阵阵感到酸楚。人退休就意味着老了,人一老就爱凑热闹,就会感到孤独,毛永忠何尝不是这个想法呢?后来,胡伟军向我详细的把毛永忠退休之前遇到点事和我学说了。我听了,觉得毛永忠的作法是正确的,是正义之举。但是,领导对他能满意吗,难怪他老伴发牢骚。
事情的经过让我对毛永忠更加刮目相看了。就在毛永忠退休的头一年的9月23日,珍珠岗——矿山专用线出现了一启因挤岔子造成的脱线事故。那天,毛永忠在北边扳道房顶班,负责专用线的扳道员吴明义,因公事脱离了岗位,造成了货车脱线,事故的责任者受到了处份。为了保住万天无事故的荣誉,大龙山车务段娄段长下令把这件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向上边隐瞒了事故。后来,铁路局知道了这件事,派来了调查组。大龙山车务段领导听说后,毛了,如果这件事要是让路局调查组知道,珍珠岗车站万天无事故的成绩一下子就付之东流了,好不容易树起来的一面旗帜将一下子就倒了。娄高松为了这事召开了紧急段务会,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典型,不能让这面旗帜倒下去!娄段长下了死命令,如果谁把这个事故透露给调查组,段里将追究责任。会议一结束,段里的有关领导按分工,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场捂盖子行动。
由于事故出在9月23日,路局叫做9.23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下来那天,他们没直接下到珍珠岗,而是先到了大龙山车务段。调查组的举动无疑给大龙山车务段隐瞒事故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娄高松亲自陪调查组到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调查。吃喝是纽带,是桥梁,是沟通感情的最佳办法。大龙山地处长白山区,这里没有海鲜,但这里却有山珍,有在大城市吃不到的飞禽走兽的肉,有味美营养的蛤蟆,有老松江里的鳖花,金鳟鱼。娄段长是在大龙山城边一个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的山庄请的客。娄段长很会办事,他害怕调查组拒绝他的吃请,便撒个谎,说是到山庄看看长白山的枫叶,欣赏一下长白山金秋的迷人景色。调查组的人可以拒绝吃请,可以拒绝收礼,但是,难以拒绝名山大川的倚丽景色的诱惑。谁都知道,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要不是来调查珍珠岗9.23事故的事情,哪能有这么好的机会一览长白山雄伟壮观,气势磅薄的景色。调查组的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他们对娄段长的邀请没有拒绝,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大龙山车务段出了两辆面包,一辆奥迪,用了三天的时间。第一天去了松江镇,住在长白山主峰脚下的松江宾馆,住在宾馆豪华的包间里,抬头就可以望见那巍峨耸立的长白山主峰,可以看见那“哗哗”一泻而下的瀑布,那神奇的,蒸发着热气的温泉。调查组的人醉了,被长白山的美景陶醉了,他们忘记此次来的使命,完全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了,他们俨然是一个旅游团体。
两天四游长白山,吃着长白山特有的山珍野味,使调查组的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每个人的心里都美滋滋,满脑子是美不胜收的长白美景。大家都陶醉在神话般的仙境里,心里都有着对娄段长的无限感激之情,大家都对9.23事故有着淡漠的观念。待大家返回大龙山,在那个美丽山庄的豪华包间里坐定之后,发现了有个打前站的不速之客在这里等候。娄高松向调查组的人一一作了介绍。原来这位不速之客不是别人,而是珍珠岗铅锌矿矿长,姓辛,叫辛树林。这个辛矿长四十出头,人长的比较帅气,说话比较干脆,干练,办事八面玲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官场上混久了,脑袋特别活泛的社会油子。调查组的人立刻明白了,这顿饭一定是辛矿长做东了!当大家坐定,酒菜上齐的时候,酒菜的质量更让大家瞠目结舌了,有熊掌鹿肉,狍子肉,蛤蟆野鸡仨儿半鸡。鱼类有鳖花,金鳟江鲤鱼,鲫鱼,鲶鱼加马口。就连素菜都是新鲜的山野菜,有蕨菜薇菜。龙须菜,猴腿,猫抓,刺五加。酒当然也很够档次了,白酒是五粮液,啤酒是天池水酿制出来的清水泉,整个餐桌就是一个山珍大全,让调查组的人砸舌,都觉得不虚此行。更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有人竟然盼望大龙山车务段能够再多出事故,好让大家有机会一游长白山,一饱口福的品尝到山珍极品,何乐而不为呢!酒桌上,辛矿长把事故的所有责任大包大揽地揽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说专用线的道岔子是他们自己扳过去的,与扳道员毫无关系,不能把事故算在珍珠岗车站,更不能算在大龙山车务段的身上。辛矿长侃侃而谈,情绪有些激动。调查组的人听了他的话都非常高兴,虽然大家的心里都有面镜子,都能够窥视出辛矿长和大龙山车务段的暧昧关系。辛矿长的口才好,思路敏捷,他可以把大龙山车务段摘得干干净净,把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故统统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可谓用心良苦。调查组的人也都心知肚明,谁不愿意把这个责任事故一推六二五,把大龙山车务段摘个干干净净,这也是调查组求之不得的事。就这样,调查结果算到了铅锌矿的头上,这个事故算路外的事故,打入了其它。调查组回去以后向局长做了汇报。调查组的人走时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大包蛤蟆油。(价值上万元)可娄高松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忘了,既然事故的责任是路外事故,那就不应该有事故的责任者,更不应该给扳道员吴明义背上一个处份。调查组一走,事故调查的结果一公布,在整个车务段引起了轩然大波!吴明义要求撤消处份,扬言要到路局告状。这一下可吓坏了娄高松,他满以为这件事可以对路局瞒天过海,包裹得天衣务缝,把事故的责任推得干净利索,典型保住了,乌紗戴稳了。可当他听说吴明义要上告的时候,他慌了手脚,他见事不妙,亲自跑到珍珠岗,他首先找到正在哈腰清扫道岔的毛永忠。一见毛永忠,他诚惶诚恐地喊了一声:“师傅!”
毛永忠瞅瞅娄高松,嗡声嗡气地挖苦说:“是娄段长呀,你咋有空到俺们这小站来了?”
“师傅,瞧您说的,到哪儿您也是我的师傅,我是特意回娘家来看看您老。”毛永忠头不抬,眼不睁,对娄高松的到来不冷不热,不屑一顾。娄高松是何等聪明的人呀,他一下就觉出了毛永忠对他的态度不对,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毛永忠还在清扫道岔,(他负责的道岔总是保持得铮亮)他也没让娄高松进扳道房坐一会儿的意思。师傅的态度使娄高松感到十分窘迫,进退维谷。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垂手站立在毛永忠的身后。毛永忠直到把道岔清扫完后才直起腰,往铁道上磕磕条帚,又瞅瞅娄高松那尴尬的样子,他也觉得可笑,觉出了自己对娄高松的冷淡,让他很难堪。想一想,觉得有点做得过了头,不管咋说人家也是段长啊,想到这,他这才客气地说了句:“走吧,有啥话进屋说吧!”
娄高松跟着毛永忠进了扳道房。一进扳道房,毛永忠指指通共不到一米二长的小火炕,说:“坐吧,我这你也知道,条件简陋,也没啥招待你的。”毛永忠在一个仅有的板凳上坐下,娄高松也在小炕上坐了下来。两个人对这视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开口,扳道房里的空气显得紧张了起来。这种凝固的气氛持续了几分钟后,娄高松咳嗽了一声,清清嗓,慢条斯礼地说了话:“师傅,咱开门见山吧,我今天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一件事……”娄高松说到这,觑眼瞅瞅师傅的表情。毛永忠坐在板凳上默默无语。
“师傅,您听我说话。”娄高松对毛永忠的洋洋不采,心里虽然不满,但嘴上又无法说出来,只好提高个声调。
“你说吧,我听着哪,又不是耳朵背,你喊什么,以为是在开职工大会呢?这就咱俩,而且又离的这么近。”毛永忠显然对娄高松的高音不满意。娄高松立刻反映出师傅的意思,欠意的笑一笑,说:“师傅,您理解错了,我刚才是怕您听不见。我今天来就是想求师傅,以你的威信,和那个吴明义说一声,别让他再告了,他这么闹下去对他没有什么好处,这不是窝里斗吗,把咱们的红旗撅了对谁都不好,……”娄高松说到这,毛永忠睁大了眼睛,怔怔地瞅着娄高松,把娄高松瞅得不知所措,心里有点紧张。毛永忠瞅了一会儿,嗡声嗡气地说:“娄段长!”
“师傅,您别叫我段长,还是叫我小娄的吧!”娄高松急忙更正,他的心里也猜出毛永忠要说的下文是什么了。他没有办法,只要能把吴明义安抚住,脸上挨点热的没什么。他尴尬地笑了笑,又说:“师傅,您在珍珠岗及到大龙山车务段都是德高望重的,人们都信服您,这件事就全当是师傅您帮助徒弟我了,我没法找吴明义谈!”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也就把话明说了,你们这些当领导的未免太缺德了吧,只管保住安全生产,保住假成绩,你们却忘了你们这么做是在伤工人的心,你们弄虚作假,隐瞒事故,这个后果你们想过吗?你们把事故隐瞒了,却对事故的责任者进行了严肃处理,吴明义能服吗? 这下可好,他要到铁路局告你们了,这件事你让我怎么说?”毛永忠很气愤(待续)

张天真简介:
从18岁开始在《吉林日报》发表第一散文开始,每年陆续不断发表。先后吉林省《今天》、《参花》《萌芽》《中国文学》《鸭绿江》《中国铁路文艺》《吉林电台》《满族文学》《长白山》等杂志发表数篇中短篇作品。如发表在《鸭绿江》杂志上的《酒鬼新传》,《萌芽》杂志上的散文《打扮春天的人》,《中国铁路文艺》杂志刊登的《三进珍珠岗》……